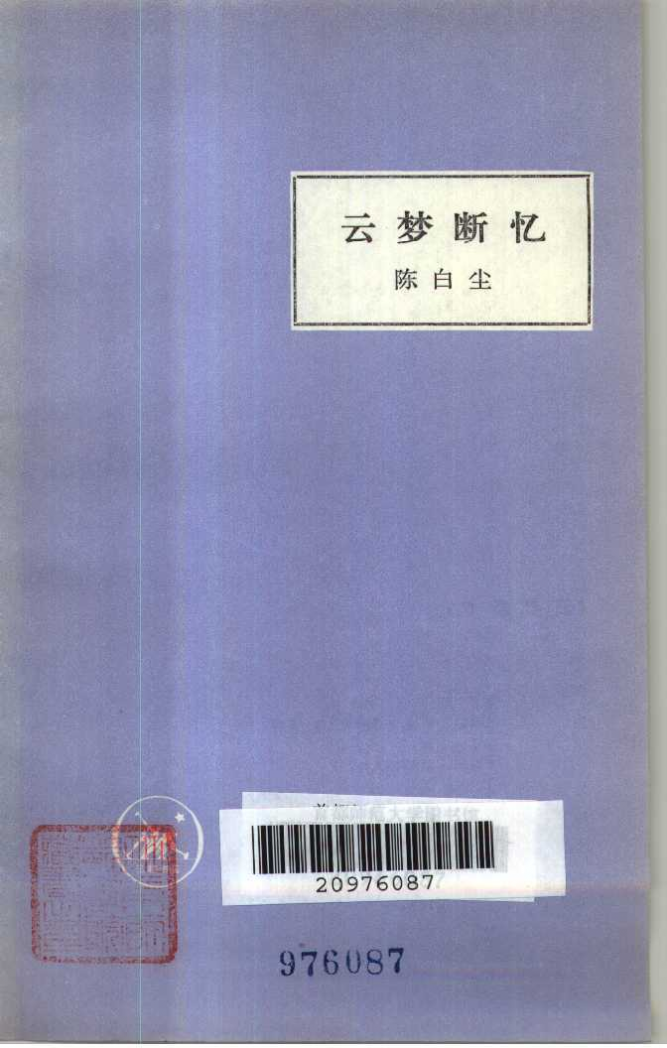忆云梦泽
陈白尘

1970年初,我终于到达梦想已久的古云梦泽边那个五七干校。这是当时北京文化艺术界人士“荟萃之所”,据说总数应达一万人,实到的已有五七千人。单说作家,我就见到过冯雪峰、沈从文、张天翼、谢冰心、臧克家、楼适夷、严文井、李季、郭小川、孟超、韦君宜、侯金镜、冯牧,以及张光年、李又然等等不下百人。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门的头头脑脑,大概都去了。我虽是从南京被揪回北京的,在经过三年多大轰大嗡、神魂不安的日子之后,能在农村享受恬静的田园生活,真是心向往之的了。更何况那些先头部队去视察过的人们回来说,那儿是如何山清水秀,又是鱼米之乡,怎能不动心?至于说那儿蚊虫多,地近沼泽等等,自然不在话下:蚊虫叮人,总比恶语伤人要好受得多,何况还可用避蚊油当胄甲。1969年下半年起,我就翘首以待,希望榜上有名了。自然,这种干校主要是为“革命群众”而设的,我类“黑帮”,只能附骥尾。就是说,在每批下去的名单的末尾,总要点缀几个我类人物,以便在“革命群众”监督之下,接受再教育。天可怜见,在第一批名单居然名“超”孙山。我当时颇似范进中举,欢欣若狂,虽然并未真个发疯。可是接近出发时,又没获得通知,这一瓢冷水浇下来,还不是去得成、去不成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我这个“黑帮”“罪孽深重”,连接受再教育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无形的宣判!我这略敢于平视他人的头,只得又低下来。后来慢慢细想,冰心、天翼等人罪行是低于我的,还有和我处境相似的光年等人,也都没被批准下去。这一比也就心安理得,在当时文联那座颇为空旷的大楼里又“安居乐业”起来。我是能够“知足常乐”的人。
当时在文联大楼里留守的,除了几位专案组的同志以外,就剩下五七个和我不相上下的人物了。当然,也还是有分别的:邵荃麟同志等也属专案组所管辖,但已没有丝毫行动自由。他住在我的邻室,除了早晚听到他因胃病而发出的连续不断的打嗝声之外,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冰心和天翼又较我自由。冰心可以每天回家,天翼也可以回家,但那时他已无家可归,只好屈尊和我们同住大楼。只有光年的地位和我几乎相等,同属一个专案组,同住一个房间,同有星期日放假的“自由”,但又同样不许回家。于是“二张”和我便在每个星期日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出游。其日程多半是这样:天翼先自由地走出大楼,在王府井大街上漫步相候;我和光年同去专案组请假洗澡,然后便作三人行了。洗澡也是真的,我们先去华清池洗个盆浴,约莫在上午10时许,去东风市场逛逛旧书门市部,但每每无书可买;然后便是出游的“主题”——进行会餐了。由于不愿走远,会餐的地点不外三家:东来顺即民族饭庄、东风餐厅和帅府园的全聚德。自从东安市场改建为东风市场以后,正如许多剧种都改唱京剧样板戏一样,原有的上海菜馆、四川菜馆、湖南菜馆都被统一在东风餐厅的二楼上了。所幸当时这二楼餐厅的菜单中还保留有几样上海口味和四川口味的菜,但又不敢明白标出,只有内行人心领神会就是了。我们三个人都爱南方口味,所以去东风餐厅的次数独多。它的炒鳝糊、红烧头尾、烧划水还是保持着原来“五芳斋”特色的。特别是头尾与划水,北京人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备货不多,但我们每次都能尝到。会餐也有分工的:天翼虽然爱吃,但他不会做也不会买,他的任务是占领座位,虽然那时饭店并不太挤——干部都去干校了嘛!光年管买酒和拿杯筷。至于点菜、结账等等,自然是非我莫属了。因为我到底是干过秘书长之类工作的。我们微醺之后,便赋归去,大约都在下午3时以后了。这是我们在北京“牛棚”中最愉快的时期:急风暴雨式的批斗,连篇累牍的检讨和应接不暇的外调都已过去了,每星期于读书、看报之余,还有此半日游的“自由”,怎能不知足呢?有人把我们这类“牛鬼蛇神”的生活写得完全阴森恐怖,也算是犯了“概念化”的毛病吧!
自然,好景不长,约莫3个月以后,亦即1969年和1970年之交,突然一声令下,我们这个“三角同盟”被解体——全都允许去干校了。这当然是好事,但事出突然,而且两天之后便启行,不免手忙脚乱起来。
于是置蚊帐,买胶靴、手电,理衣衫、书籍,钉木箱,打行李,整整忙了两天。而跑遍全北京城,手电缺货,只好买了只自行车灯为代用品。胶靴更无购处,便向南京家中求救。最后,还有一件大事,“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嘛!下得乡去,哪能不多带几文钱?专案组规定我每月只用25元,平心而论,也不算少;可是订报、买书、交党费,在伙食费之外还有“三角同盟”费,实不够用。所幸北京有几位朋友处可以随时借贷,于是便向一位电气工程师经强士同志打电话,借了200元。他的全家闻讯,还在东华门大街一家小酒铺里偷偷为我饯行,又喝了两盅。有了200元,自然胆壮,便去百货大楼买了两罐云南火腿,私藏箱底。因为据传闻,那个鱼米之乡,自从去了几千吃客,鱼虾都不敢上网了!
在京广车上,虽是坐的硬席,但为我们几位六十以上的老人买了三张硬席卧铺,轮流去睡。比起1966年我被揪回京时的情况,这真是“皇恩浩荡”了!车上还有幸遇到老作家沈从文。他有心脏病,也被批准下来了。大概在1961年,在我所编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他一首旧体诗,当时颇得好评,但在1966年也成为一条罪状。我的罪状太多,这不算一回事。看见他自然很高兴,因为他的夫人张兆和正在我们干校,此去自可团圆了。但他却笑眯眯地说,那可不能。因为虽是同一干校,但所属单位不同,还得做老牛郎。他那圆圆的脸上永远是挂着微笑的,虽然那时他已体弱多病。后来听说他被“照顾”到丹江口去了,虽逢七夕,和老织女也难相会了!
第二天,我们终于到达自己的干校了。卡车上还有在北京留守的“革命群众”,所以先到的人们还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我们这些“黑帮”是沾光了,但都很自觉,退居一边以清界限。可是连、排、班长们还是用手车把我们的行李分送到各人住地——当时校舍尚未动工,我们都分别住在当地老乡家的余屋里。我的房东姓贾,这儿便叫贾家湾。这地方没有大村落,每个水湾聚居三五户至七八户人家,因此我们这个连队便只好分散在三四个居民点里,而连部的食堂便设在贾家湾,吃饭、打水都很方便。看来我是被照顾的了。
我们这干校的所在地被人们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叫“向阳湖”。但我并未看到湖,除了附近两个大水塘。据一位有嗜古之癖的“革命群众”考证说,这儿一带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在四周丘陵地带中间有很大一片沼泽地,正证明它是云梦泽的遗址。当年云梦泽很广阔,自然不仅限于这点地区,否则秦始皇不会从咸阳来旅游,而汉高祖也不会托游云梦而借此擒拿韩信的。也许因为韩信是我的同乡,我喜欢叫它云梦泽。这是否因为联想到自己也会在云梦泽被擒呢?那倒没有的,因为我手里并无兵权,还不够格。不过因为并不喜欢那个新名称而已。这地方,阴雨很多,其实是少见阳光的;况且在“史无前例”的日子到来之后,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更改姓名,以示“革命”的事例很多。想到他们,总觉得肉麻。比如有位女性,因为父亲不够光彩而改从母姓,并且改名“忠青”。这就是以肉麻当效忠了;可是江青一倒,她只好连忙再次改名换姓,可惜已经迟了!因此,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叫它云梦泽的好。何况它既然无湖,而沼泽地却到处可见,这也算是忠实于历史吧。
自然,如果遇到地理学家,定要循名责实起来,也是不妥的。如今这儿除了残留着几处荷塘而且又被我们这群“农业专家”给毁了以外,实在想像不出它烟波万顷如云如梦的丝毫景象来。有的只是大片沼泽之中,间有几块“无名高地”和一条小河。到处荒草丛生,却无一株树木。水禽是有的,野鸭和雁群有时也暂时栖止,隔夜便又飞去。3年之中,我曾见到过一只白鹤,但仅仅是一只,而且也仅仅是那么一次。飞禽呢,大概是无枝可栖,很少;有的是白颈乌鸦,又很讨厌。另外,只有但闻其声的云雀,在高空里自得其乐地歌唱,也并不多。至于走兽,除了放牧的水牛之外,很少见到什么。即使是牛,如果离开牧童,深入沼泽地带,它也“不能自拔”,每每陷死泽中。许多整架的牛骨在沼泽地附近时有所见,足以为证……
就是在这样不毛之地上,我们的干校却企图创造出一座世外桃源来。另一种说法则是:让我们这一群文化人从此在这儿扎根落户,彻底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永远也不让回到原有的文化岗位上去。这可是彻底“革”去“文化”的“命”了!这一说法也似有根据:其一,动员下来之前是特别强调扶老携幼,全家下放的。其二,是当地农民为我们编的顺口溜。其词曰:
“五七”宝,“五七”宝,
穿的破,吃的好,手上戴着大手表!
“五七”宝,“五七”宝,
种的多,收的少,想回北京回不了!
关于“‘五七’宝”,得先做解释。当地老百姓对孩子们的爱称,都在其名字下加个“宝”字,如名永福,便叫永福宝。我们的干校叫“五七干校”,干校的“革命群众”自称“五七战士”,但老百姓却毫不客气,下自青少年,上至老头子,一律称为“五七宝”。这是爱称还是贬词,待考。不过这末句“想回北京回不了”,确是道出天机了。当地县委是会了解我们干校上级意图的,否则一般老百姓如何敢于下这讽刺性的结论呢?
关于“种的多,收的少”,也是实情。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不会种地或不按农时。老百姓还有三句话概括得好。他们说我们是:
大雨大干,
小雨小干,
晴天不干!
“大雨大干”者,因为我们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者,雨下得越大,干得越欢,才显出革命精神。但有一天已经下雨了,正在收割麦子的人说:“收工吧,不能收割了。”但我们连长以无比豪情叫喊道:“跟老天爷斗争到底!”麦子自然都割下了,但老天爷不买账,一连下了三天雨,收到手的麦子都烂掉了!“小雨小干”,不用解释。“晴天不干”又是为何呢?答曰:“要开会!”革命要讲纪律,连部既定的计划,该开会的日子就得开会!此所以“种的多,收的少”也!
平心而论,我们干校是有不少建设的。首先,围湖开垦,就筑了一条周围十余里的大坝,宛如一座土城,这是一铲一铲泥土堆筑起来的。而大坝四周就便挖了条宽约二丈的壕沟,仿佛护城河。其次,修道路,搭桥梁,大坝里四通八达了。再其次,半年以后,各个连队都建筑起一排排简易砖瓦平房,而且还装上电灯。最后,即使“收的少”,但在大坝之内万亩良田里,到底也收了不少粮食;而菜园种的蔬菜,猪栏里肥猪和所饲的家禽,大致也接近自给了。至于这些成就花了多少钱,那是只算革命账,不该算经济账的。我和侯金镜同志等人都当过鸭倌,三人工资总数约400元以上,加上饲料等等,则我们收获的那些可爱的大鸭蛋的成本,大约要高出市价五倍以上了!但这笔账谁敢算呢?那等于是反对走“五七道路”!我们连里有支歌曲,其中有句“要五七道上迈大步”,是天天听到的。可是每次听到“迈大步”三个字,不知怎地,我总想起幼年时候在我那小县城里走街串巷“卖大布”的山东人的叫卖声。自然,这一联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识。尽管我每周都写一份“思想汇报”,坦白说,这些思想是没有写进去的。
个人收获更大。鲁迅说阿Q是: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舂米便舂米,并因而获得“真能做”的赞语。像我这样“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知识分子,经过三年多的锻炼,大致计算一下,从薅秧插秧到种菜园,从做建筑小工到筛沙运砖,从挖土浇水到拉车挑粪,从拾牛粪捡麦穗到割麦割稻,一直到守夜和牧鸭群,大大小小工种学会20多项,可说比阿Q更能做了,但我从未获得半句称许。因为我知道:身非“革命群众”,只有被监督劳动之份。但我还有个很重大的收获,经过不断劳动,原来每年都要犯一两次腰椎炎的,一犯病便得卧床半月,下去以后却基本上未犯。有一次似乎要犯了,一位女医生为我打了一次封闭针,又能劳动了。“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倒的确是真理!
有位高干,是别的连的,在建筑房屋劳动中,他任挑运三合土小工,很起劲,并发表感想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一挑起扁担,官僚主义的架子就全垮了!”它很得干校领导的欣赏,便到处引用,加以表扬。这句话也确实是真理。大公鸡是以它美丽的羽毛,特别是那高高翘起的尾巴上的长羽,才显出它的雄姿的。但我在干校附近某一老百姓家里却见到这么一只大公鸡,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主人家将它那高高翘起的尾部羽毛全部剪去,它的体形顿然缩小了一半以上,剩下的前半部虽然羽毛如故,却委实不成样子,别说是雄姿了,连秃尾巴的母鸡也比它好看得多!我想,人们的官僚主义架子大概也像那大公鸡的尾巴吧,一旦剪掉,就是说,挑起担子,那雄姿的确无影无踪了。可是我不知道那被剪去尾部长羽的公鸡,将来是否会再生长起来,恢复旧日雄姿?也不知道那位挑三合土的朋友,一旦回到北京官复原职,不知是否会再长起长长的尾羽来?呜呼!人的改造到底很难哪!
再说我们那干校,最初两年,确实兴旺,热闹了两年;生产是热气腾腾,“革命”更轰轰烈烈。特别是阶级斗争不断有“新动向”,“革命”浪潮便一浪高过一浪,至于那个清查某种分子的运动,更是搞得热火朝天!但到1970年“九一三”事件,即林彪折戟沉沙以后,热潮逐渐减退了,许多热情的“革命家”也不讲在干校扎根一辈子,而开始考虑起个人的出路来了。一位最最革命的“女革命家”,首先以“革命的需要”为理由,被校领导调离干校,由本省某机关所接受,重新当起革命干部来了。原先她是全家下放,连同沙发、家具都搬下来的,又全部搬回省城。但她毕竟不够有远见,不久,北京来了电报,指名调走三名高级干部,由国务院分配工作。“女革命家”愤懑了:为什么最最革命者却留在省城而不能重返首都呢?后来她也毕竟回北京了,但费了不少手脚和时间,总未成为“最最革命”的人物,殊属遗憾!但经过这两次调动,人心浮动,自不待言。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大有好转,友谊又逐渐抬头;一些曾被斗得很惨的人,也有人敢于和他接近。既然某些高干能官复原职甚或升迁,则某些走资派的房间里自然也应该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了。
到了1972年底,探亲便形成高潮。有事无事,都可借口探亲,回趟北京。有一位同志的理由是丈母娘到北京,他还从未拜见过,这也可以被批准。于是北京来份电报,都可以回去一趟。特别是新年和春节前后,偌大一个连部里,剩下的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这可苦了别人:一是当地粮管部门,他们全县的全国粮票本来有限,各连部探亲的人数以千计,都得携全国粮票回京。无法,只得向北京要求支援。二是各连的伙房,人少了,本来可以省事了。但矛盾在于猪。最初是人多猪少,不够吃;如今可又人少猪多,吃不完。这可真是“人少畜生多”了!于是伙房里三天两天宰猪。吃一顿饺子每人可以发净肉馅一斤,面粉一斤,白菜自取,概不限量。可是肚皮毕竟有限量,这一顿饺子够我吃两三天的!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我原是较长期的专业鸭倌。不用说,在这情况下,鸭群早被宰完,我失业了。于是派了我另一项任务:守夜。守夜共两人,一人一夜,轮流“执政”。守夜并不需要体力,只要整夜坐在值班室里听狗叫,如有响动,用手电筒向四周探照,并大声吆喝一下,表示“有守夜人在此,休得无礼!”其实我们这四排平房,并无围墙,真有个大胆而身强力壮的小偷前来,我这当时六十三四岁的糟老头子,也未必管用。但稻草人还可以吓走麻雀。我总比稻草人强多了,所以也颇有自信。所苦者,“众醉独醒”是表示超人,而“众睡独醒”却颇苦闷寂寞,难熬煞人!虽然有夜宵可吃,但每夜即使吃上两顿,也不过花费一个小时足矣!其余11小时如何熬过?值班室是在阅览室里的,倒有几十本书,但绝无新著。范文澜同志主编的《中国通史》初版本,延安出的,是唯一可读之作了。但也经不住三四个晚上就读完。当时又值隆冬,只有走路暖足,兼驱睡魔!可是盼到早晨6点下班了,我虽可倒上床去,可别人又纷纷起身、上工,反而睡不着了,必须到晚上才真个倒头大睡。如此,我是两夜并在一夜睡,而第三天又轮班了。比较下来,这12小时并不劳动的守夜,比16个小时的牧鸭生活更苦。因此,不到一个月,大慈大悲的女医生诊断我心脏有病,血压偏高,主动给我一星期的病假。一星期后复诊,病情未见好转,只好再休息。
这时在南京家中留守的金玲,已患极度神经衰弱症,又听到谣传说我已被批准回南京,便三天两头电报来催问归期。我们干校虽然毫无所知,但怕我真个病倒,也就批准我3个月病假,回南京医治,这正是探亲假高潮时期,所以也就从宽了。以后呢,每3个月续假一次,未再回到云梦泽了。不过我每月汇去党费,干校每月寄来全国粮票,保持着这一线联系。1975年8月,专案组给了我一个结论,尽管我不同意,但这一线联系也断了!再不久,连那干校也撤销,“迈大步”的歌声歇了,房屋和良田都送给地方,经济账和革命账都一概不算了!
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可歌可泣,可恼可恨的事自然很多。但回忆总是蒙上彩色玻璃似的,因而也是如云如梦,总觉美丽的。因此,即使可恼的事吧,也希望从中找出些可喜的东西来。但不知这支稍嫌油滑的笔可听使唤不?
云梦泽确是值得回忆的。
本文选自《陈白尘文集》第6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